范约翰担任了五年副主任的沉重职务后,终于不得不回到英国休息,剩下戴德生独力主持大局,不能离开上海。 「亲爱的侯尔道,」戴德生写信给伦敦内地会内务主任说:「你很难了解这边的情况,我要了解和爱护我们亲爱的同工,聆听他们的愁苦和困难,他们的失意和挣扎;而且知道有人患病,有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收到在急难中要求指示的电讯,或是报告有人去世时,给子恰当的指引;收到屠杀、纵火的报告,还有各种不同的事故作出适切的行动;再加上日常的职责,以及应付一个将近五百人的差会在经费上的需求,真使我疲惫不堪。 只有一个方法使我不至于倒垮了,就是把各样事情带到我们的主面前。 他必定帮助,他必能了解。」
中国委员会修改内地会的《原则与实践》和《协议书》之事,使伦敦委员会某些成员不满。 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1890年,引致近三十位传教士辞职。 戴德生也指出:「撒但确实十分忙碌。」 戴德生不在伦敦时,伦敦委员会有些事情没有通知他。 海恩波因为参与反鸦片运动而分心,似乎不能专心作中国内地会的行政工作,但海恩波认为这样的指摘对他非常不公平。
也许伦敦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之间的对峙是无可避免的。 戴德生本来希望中国委员会有执行的权力,运用各区监督的经验去处理每日碰到的实际问题。 可是,伦敦委员会自视为中国内地会的总会,其余各地的委员会不过是辅助性质。
沙威廉(William Sharp)提出由伦敦委员会掌握最高权力。 他认为伦敦委员会要向中国内地会在华工作的支持者和捐献者负责及交代。 沙威廉说话尖刻;他对戴德生说:「你的委员会不应徒具虚名,它应有实际的行政权力,当它跟你的观点不一致时,你总试图强逼委员会接受你的观点。 我希望你可以容许差会自行运作,而你自己可以集中精神去阐释圣经,以及激励教会。」
让伦敦委员会掌握大权,有违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的基本原则——以中国作指标。 当伦敦委员会干涉一些传教士反对《协议书》中某些方面时,戴德生的反应是:这是工场的事,不是母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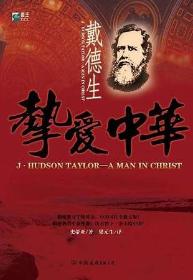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